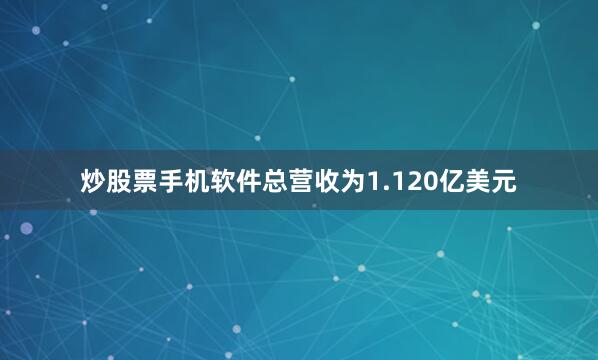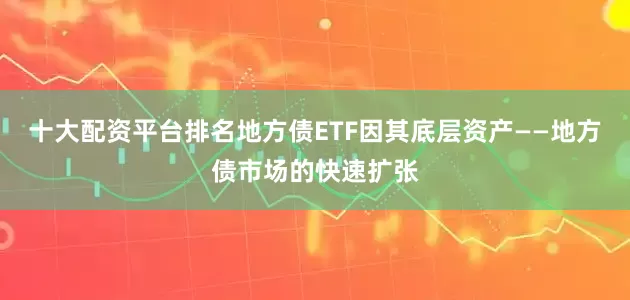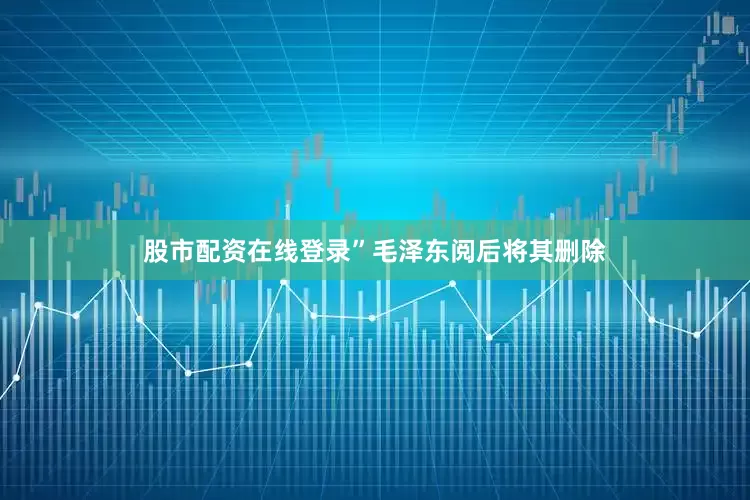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战火硝烟中,面对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角逐,“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党际复杂局面、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骂声”频频,以颇具革命色彩的对外舆论斗争树立起了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崭新形象。尼克松都不禁赞叹: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有着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民和庞大自然资源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外舆论的斗争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群体的胆识、智慧和实际行动。其中,毛泽东的哲学思维、战略眼光、博大胸怀以及灵活的斗争策略尤为突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以“钢少气多”概括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武仗”取胜的奥秘。在同样残酷的对外舆论斗争中,毛泽东所展现出的坚定意志、自信底气、平和态度、勇猛气概以及敢于斗争的精神,为我们如何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承前启后、主动应对挑战,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借鉴。
坚定理论信念、拓宽胸襟视野:毛泽东引领对外舆论战场的豪情壮志
“他们虽然一时嚣张,但最终必将走向崩溃。”

1957年11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我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出席了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风过耳,万事如烟。中华悠久文化之包容与宽宏,亦孕育了毛泽东在遭受非议时的气度与胸怀。当古老东方的千年智慧与文化自信遭遇仅百年历史的某些西方国家的碰撞与冲突,差距显而易见。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参考资料》刊载了一篇美国合众国际社对我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诽谤报道。毛泽东阅读后,于电讯旁批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高髻危冠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其非凡的文采与气魄跃然于纸面。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中苏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我国驻外使馆反馈称:“苏联《真理报》不再报道我国消息,甚至将‘中国’二字抹去。”毛泽东对此批示:“螳臂挡车,不自量力。”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修正主义者不断对我们进行指责。我们的立场是,任其指责。在必要时,给予适当的回应。我们这个党已习惯了别人的指责。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国外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指责我们;国内有蒋介石、地富反坏右指责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如此,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是否孤立?我并不觉得孤立。这里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难道会孤立吗?”此言一出,会场中爆发出一阵笑声。
洞察规律、深谙本质:毛泽东引领对外舆论斗争的坚实“底气”
“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应遵循规律而行,否则,工作难免陷入困境或误入歧途。”正因洞悉了对外舆论斗争的规律与本质,毛泽东得以指导全党,使他们具备了不畏“骂名”、勇于斗争的信心与勇气。
毛泽东曾言及对“我们”进行指责的人数:“那些指责我们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其实不过是少数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动和半反动分子,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分子。这三类人总计可能只占人类总数的极小部分,大约不超过百分之五,甚至可能不超过百分之十。如果我们假设在一百人中就有十人持反对意见,那么在全世界27亿人口中,也只有约2.7亿人表示反对。相反,有超过24亿的人支持我们,或者至少是中立,甚至可能因为被敌人误导而对我们抱有疑虑。”通过比较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数量,我们不难看出双方的力量对比。

1959年十月,毛主席在北京热情接待了来访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面对那些反华势力的攻击与诋毁,他们的行为并非持续不断,而是间歇性的。他们往往以某些特定议题为借口,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一时的反华活动。然而,这样的借口并不能长久,因为他们的论调缺乏合理依据,超过九成的人都不相信他们的言论。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攻击,只会让自己越发陷入困境。尽管美国与我们之间的仇恨可能更为深重,但他们的反华行为同样具有间歇性。原因在于,无端地持续攻击只会让人感到厌烦,市场份额随之缩小,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随后,他们会寻找新的议题,以再次挑起反华的风波。如今,反华势力的攻击已呈现一定的间歇性,未来甚至可能出现更长时间的间歇。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工作的成效。揭露反华势力的手段和伎俩,让其暴露在阳光下,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关于“骂”我们在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效应,毛泽东曾明确指出:“首先,这些人寥寥无几。其次,他们的反华行为对我们并无实质性伤害。第三,他们的反华行为反而能够激励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立下壮志,务必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赶超那些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自讨苦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民众面前,暴露出他们自身的丑陋面目。因此,对他们来说,反华是恶运,对我们却是福音,这证明了我们确实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证明了我们工作的成效显著。对他们而言,则是祸端,而非吉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刻阐释,为全党在对外舆论斗争中确立了必胜的信念。
毛泽东向来擅长辩证地看待问题。在对“指责”我国一方的论述进行剖析之后,他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面对“指责”时应坚持的基本准则。
“不批判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便无法进步;不批判形而上学,辩证法亦难发展。批判的过程,离不开对对手材料的掌握。”1959年9月4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的秘书胡乔木,以及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下达指示:“对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有利评论,应大量刊登;即便是污蔑之词,亦应予以发表并加以驳斥。越是对华恶毒的攻击,越能凸显我们的有利之处。”在中苏论战中,面对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发起的攻击,毛泽东以雄文反击:“我们勇于全文刊登你们的一切言论。在刊登了你们所有对我们的‘伟大’进行痛斥的作品之后,我们将逐一或简略地予以驳斥,以此作为我们的回应。有时,我们仅刊登你们的错误文章,而无需一字一语的回答,让读者自行思考。”
“移交仪式上,应大力宣扬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阐述我国援建××××工程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忠实地践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国际主义教导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阅后将其删除,并批示:“此类做法过于强加于人,切不可如此行事。”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再次指出:“若仅片面地展示中国,夸大其优点,实属不妥。当然,全盘否定中国也是错误的。我国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偏爱夸耀成绩,不愿揭露错误,因此你们需注意。其他国家亦然,既有优点,也有不足。”
广结良缘、讲述佳话:毛泽东引领对外舆论斗争的“和谐之道”
“中国人民欢迎一切旨在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举措,并期待这些努力能够取得成功。”面对一些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与我国产生矛盾,毛泽东不计前嫌,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成功实现了以斗争促团结的目标。1956年2月10日,在会见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时,毛泽东说:“你们目前正面临困境,需要逐步推进,务必根据实际情况行事。在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都能理解。”毛泽东还对外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区分,致力于团结各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961年10月7日,在与前来洽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文版翻译和出版事宜的日本友人交谈时,他指出:“在日本,除了那些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之外,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是我们的忠实朋友。你们也会感受到,中国人民同样是你们的真诚朋友。”

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了蒙哥马利。
“新华社发布新闻时,必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与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1月19日,新华社播发了《张闻天简历》,其中提到:“在1934年至1935年冬季,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军队进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张闻天是领导组织中的一员。”这一消息在国际舆论场上引起了轰动。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27日晚,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并共进晚餐,双方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英雄之间总是心有灵犀的。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后,6月初便发表演讲,称赞“在中国期间,他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不断前进,未曾受到损害”。6月20日,蒙哥马利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我同毛的会谈》,详细叙述了他在5月下旬访问中国的经过,以及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情况,指出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人人献身且目标明确的国家;中国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拥有“充足的高素质人员”,民兵组织遍布全国,因此入侵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蒙哥马利劝告“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作为国际知名的二战英雄,他所讲述的“中国故事”,成为西方世界审视新中国的重要依据。
“你提及美国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美国政策的看法并非一致,我们应关注这些群体的情绪。在此方面,我们确实应当留意。”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发布的新闻,美国民众颇感不适,甚至反感。”因此,“需有一批人专注于研究美国,关注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上层之外,你所提到的中层、下层舆论同样不容忽视。”此后,毛泽东特地审定了“是的。无论美国是否承认我们,无论我们是否进入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不会因为未进入联合国就肆意妄为,如同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般。我们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应以战争解决问题。然而,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中国的责任,美国同样肩负重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一点我们坚决维护。”毛泽东同意斯诺公开发表此谈话,为12年后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舆论基础。
刚毅不屈、锋芒毕露:毛泽东在对外舆论斗争中展现的“虎威”
“未来定将充满光明,但必须经历斗争。若不斗争,他人怎能听从你的声音!”然而,毛泽东所倡导的斗争并非盲目蛮干,而是充满智慧、策略与胆识。

1950年,毛泽东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参加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各位代表,其中右二为新闻总署的署长胡乔木同志。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俄文译稿已经定稿,但根据主席的指示,尚未出版。鉴于当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形势与三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建议俄文本由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两天后,毛泽东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1964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俄文版问世,向社会主义阵营和俄语世界展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力量。
“以美国帝国主义官员为代表的艾奇逊之流,日益沦为如果不依赖最卑劣的谣言便无法生存的最低级的政治骗子。这一事实揭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层面上已堕落到何种地步。”“感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时,除了编造这样的谣言,已无其他更好的手段。”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斗争有“胆”,在对外舆论斗争的战场上敢于“刺刀见红”。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对此,英国、印度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内政进行攻击。4月25日,毛泽东就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批示:在宣传报道中,要“直指英印,不要躲闪”,人大、政协就此事的发言,也要“理直气壮”。5月4日,针对挪威报纸就西藏问题侮辱中国领袖,毛泽东指示宣传、外交部门相关同志:“挪报第二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说毛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人能骂神,不能骂毛,毛比神还厉害吗?如果中国不屈服,继续胡闹,那末,西方将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的独裁云云。”“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革命反革命界线问题上闹清楚。这是好题目,不应放过。挪威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1963年12月2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发表演说,批评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等等。毛泽东指示刘少奇、邓小平和外交部门:“建议写一篇文章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个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1964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对美方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文章酣畅淋漓地指出:“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
直面挑战、勇于改进:毛泽东引领对外舆论斗争的“胆识”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乃是毛泽东同志在对待批评问题上的坚定立场。面对国际舆论的纷扰,毛泽东同志深刻领悟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内部的团结以及工作的精益求精。”在遭遇非议中,他善于发现问题、剖析原因、化解矛盾,确保团结稳固、工作高效,从而使得国家日益强盛。正如他所言:“一座长江大桥,便能说服众多人心。若无此桥,他们难以置信;一旦建成,众人亲临目睹,便信服无疑。”在国际舆论斗争中,诸多难题亦随之迎刃而解。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智若愚”与“大勇无畏”的生动体现。

在国际舆论的交锋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坚定有力地反击国际敌对势力的恶意攻击和诽谤,同时,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对手,都应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注重策略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
“建议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会议,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农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958年12月22日,新华社《参考资料》上发表了日本共同社的评论文章《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其中提到:“自今年夏季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全球范围内对其的评价各异,既有赞誉也有贬低。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一大步’,故而备受关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人民公社是违背人性的制度,注定会走向失败’。”毛泽东在阅读这段文字时,多次画下着重线,并在“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败的”这句话前标注了三角符号。紧接着,他在旁边批注了“基本正确”四个字。追溯至12天前,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集中反映了党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体现了党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国,正以《决议》精神为指导,逐步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努力遏制急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冲动。
按天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